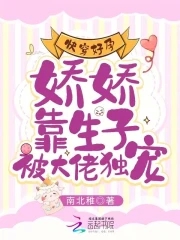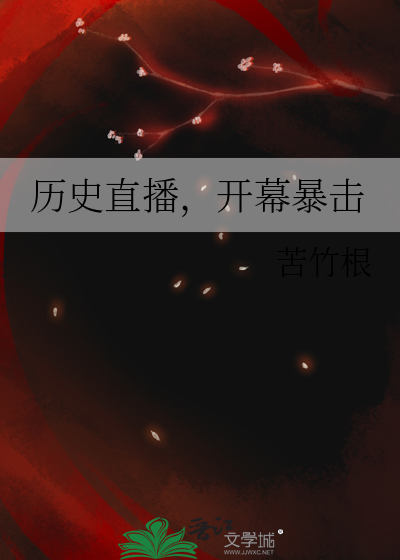小嗨书 > 明落之玺 > 第123章 葺院承囍(第3页)
第123章 葺院承囍(第3页)
“便叫囍院吧。”香玺指尖轻划过木匾上新刻的笔锋,秋阳漫过檐角竹帘,在未干的刻痕上镀了层暖金,“如今老友在侧,新院初成——这对并蒂的‘喜’字,该盛满人间烟火的温热,收存你我掌心未叙的流年。”
朱允炆望着香玺眸中跳动的烛影,忽然想起春和宫的雨夜,他曾执笔替她描眉,笔尖掠过眉峰时,她轻声说:“史书里的年号会褪色,但人间的欢喜永远新鲜。”笔锋辗转间,他故意将两个“喜”字的横画连得更紧,像交叠的掌纹般难分彼此。“欠你的那场婚礼,终能补上了。”
夜风掠过新栽的梅枝,忍冬藤蔓已攀过竹架,细碎的白花混着青苔香。香玺靠在他肩窝,听着远处溪涧与虫鸣织成的夜曲——这曾在史书里漂泊的魂灵,此刻终于在青石板上落下实实的脚印。
建文四年孟夏,南京宫墙的硝烟尚未散尽,丹陛上的青砖还渗着焦木味。
朱棣立在奉天殿台基,望着琉璃瓦缝里钻出的野草在风里摇晃——那些被战火燎黑的廊柱虽已刷过朱漆,却掩不住木纹里蜿蜒的焦裂,如同他掌纹间永远褪不去的箭伤。
礼部官员的靴声在空殿里敲出急鼓,他们捧着金丝楠木的棺椁图纸来回奔走,玉笏板上的朱砂字洇着汗渍。
望着这些蝼蚁般忙碌的身影,朱棣忽然想起徐祖辉——那个在城破时站在承天门上,袍袖被火光照成血红色的身影。
召见徐祖辉那日,殿角铜漏声格外清晰。烛影里,徐祖辉的朝服洗得泛白,襟前补子上的獬豸纹却依然笔挺如刀。
“卿若肯转身,华盖殿的案头自会有卿的一席位置。”朱棣的声音混着龙涎香,在丹墀下荡起回音。
徐祖辉垂首敛袖,鬓间银簪轻颤,惊得梁间雏燕“扑棱”展翅。抬眸间,衣摆垂落如刀裁云帛,纹丝不乱 。“蒙殿下青眼,然臣朝笏已随旧主衣冠,长埋于往昔烽烬。若要强臣重执青萍……”
话音顿在喉间,他指节狠狠掐入掌心,甲痕几欲嵌入掌纹,“除非先断这双曾捧玺绶的手!”他刻意将“殿下”二字咬得沉冷。玉笏叩击青砖,脆响沿着廊柱攀爬,如黄钟大吕,在梁柱间镌刻下徐氏百年忠烈的不朽注脚 。
殿中寂静如冰。朱棣捏紧御案上的镇纸,翡翠狮子的鬃毛硌得掌心发疼。他忽然笑了,笑声惊得司礼监太监手中拂尘落地:“罢了,长兄既钟情这方天井,那便在此间看云起云落吧。”话落时,殿外的暴雨正巧砸在琉璃瓦上,将徐祖辉被拖走时沉重的靴声,碾作细碎尘末,消散在风雨喧嚣里 。
两个月后的月夜,徐府庭院中桂香似有还无,如一层薄纱悄然铺展。密探衣角刚在影壁后一闪而过,徐祖辉便敏锐地自石凳上起身。月光倾洒,落在他熬得颧骨泛青的面庞,仿若镀上一层冷银。
“陛下与香玺姑娘,当真已在黔中安稳落脚?”待听清密探来报,他紧绷的神色瞬间一松,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他抬手,指尖轻轻抚过石桌上纹丝未动的茶盏,盏沿还凝着晨露,凉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——原来,从盛夏走到金秋,不知不觉间,这么多日夜已悄然流逝 。
剑鞘滑落在青砖的声响惊飞宿鸟。徐祖辉望着手中长剑,剑穗上的玉坠是朱允炆亲赐的,此刻正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摇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