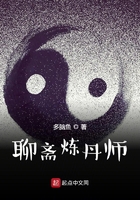小嗨书 > 神鬼复苏:自山海经开始降临人间 > 第169章 古老低语中的深渊召唤(第3页)
第169章 古老低语中的深渊召唤(第3页)
我捏了捏手里的面具,冰凉坚硬。
“我呢?开门的?”
赵清娥没接话,只是看着灰蒙蒙的海面。
船头破开灰浪,朝着那个未知的点,一头扎进茫茫大海。
前面是啥?谁也说不准。
但那地方在叫我,我得去。
面具在我手心里,烫得厉害,那股子又老又邪的低语跟钻头似的,一个劲儿往我脑子里钻。
船舱里只有发动机“突突突”的闷响,震得人骨头缝都麻。
赵清娥靠着舱壁,眼皮耷拉着,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缓劲儿。
赵大宝把自己团成一团,塞在角落里,小呼噜打得还挺有节奏。
就林队,跟根钢条似的杵在船头,背对着我们,也不知道在瞅啥。
我把面具翻过来,贴在自己脑门上,冰凉的触感激得我一哆嗦,然后闭上了眼。
嗡——
那低语声一下子就炸开了,不再是乱糟糟的噪音,变成了一种怪腔怪调的话,每个字都带着股子铁锈味儿,刮得耳膜生疼,好像是从地底下十八层爬上来的。
“归…藏…深渊…等待…钥匙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