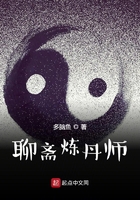小嗨书 > 神鬼复苏:自山海经开始降临人间 > 第169章 古老低语中的深渊召唤(第2页)
第169章 古老低语中的深渊召唤(第2页)
赵大宝哼哼唧唧地找了个角落躺倒:“得嘞,又得玩命,我这把老骨头……”
我走到船头,海风腥咸。
胳膊底下的纹路有点痒,手里的面具也跟着微微发烫。
心里头却出奇地稳当,那感觉怪得很,就像走了很久很久,终于闻到了自家门口烧饭的味儿。
赵清娥什么时候过来的,我都没察觉。
“你真想起来了?”她声音不大。
“不是想起来的,”我摩挲着面具,“是身体自个儿认路。天冷了,树叶就得往下掉,差不多是这种感觉。”
她没说话,过了一会儿才开口:“祭司的记忆里,说以前有过比人更老的活物。神树就是他们弄出来的,后来……好像出了大事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就记得叫‘大分离’,然后那些东西就没了。”
“神树是他们留下的?”
“也许吧。”她点点头,“可祭司觉得,神树只是个引子,真正的好东西,埋得更深。”
“归藏。”那两个字从我嘴里蹦出来。
“嗯。”她应了一声,“程天宇找的就是它。他觉得那是长生不死的门道。”
我捏了捏手里的面具,冰凉坚硬。